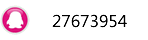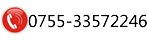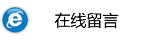“舉牌”有可能坐牢!,是美國經濟的前車之鑒
“舉牌”有可能坐牢!,是美國經濟的前車之鑒

自2015年底“寶萬之爭”浮出水面起,“門口的野蠻人”再一次為公眾熟悉。回顧2016年, ,南玻管理層集體辭職;恒大增持萬科A至14.07%,寶能、華潤、恒大三足鼎立, 萬科經營環境動蕩 ;前海人壽增持格力電器至4.13%, 董明珠面臨新挑戰 ; 陽光保險頻頻舉牌伊利股份 ,“未來12個月內不再增持”的承諾并不被信任; 平安入主上海家化后 ,致高管葛文耀、王茁離職,2016年前三季度上海家化營收同比下降7%,凈利下滑45%, 優秀國企走向平庸……
12月3日,證監會主席劉士余發表演講稱: “最近一段時間,資本市場發生了一系列不太正常的現象,你有錢,舉牌、要約收購上市公司是可以的,作為對一些治理結構不完善的公司的挑戰,這有積極作用。但是, 你用來路不當的錢從事杠桿收購,行為上從門口的陌生人變成野蠻人,最后變成行業的強盜,這是不可以的。這是在挑戰國家金融法律法規的底線 ,也是挑戰職業操守的底線,這是人性和商業道德的倒退和淪喪,根本不是金融創新。”
對此,有聲音認為,那些沒有考慮到可能被舉牌的企業家,存在管理上的失誤;,不如直接制定新規則來得有效。對此,
島君特約青年經濟學者簡練撰文,詳述為何中國要采取行動,不能重蹈美國經濟脫實入虛的老路。
本文原標題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不應受到“門口的野蠻人”的干擾》。
作者|簡練
供稿|供給側經濟觀察
來源|正和島
自2014年下半年以來,國內以一批新型保險公司為代表的金融力量,頻頻舉牌一些股權相對分散、質地比較優良的上市公司,引發市場和社會的矚目。2015年底以來,連續發生了幾起代表性案件。起先舉牌對象集中于房地產企業和個別股份制銀行,近期蔓延到南玻、格力電器等珠三角地區等股權分散、高度依靠企業強人的技術型知名企業,進而進一步擴散到中國建筑、康得新等國有、民營企業。12月3日,劉士余主席對有關行為做出了嚴厲的回應,引發社會討論。
中國激進型保險公司的舉牌行為,和美國80年代中期起盛行的杠桿收購(LBO)性質上是一樣的,對于企業的潛在沖擊也十分類似。 但是,正如美國80年代一樣,中國當前正處于改革的關鍵時期——供給側改革需要一批扎實的、進取的實體經濟企業成為產業升級的帶頭人,這批企業必須保證把握在經驗豐富、全心全意經營企業的企業家手里,不能讓資本躁動催生的中國版門口的野蠻人干擾改革。因此, 有必要在審視美國80年代杠桿收購帶來的教訓的基礎上,。
美國80年代杠桿收購的歷史背景、奧妙及后果
并購,本來是企業世界中并不少見的事情,但是, 美國80年代的杠桿收購 卻不是普通的并購,它對美國除了當時新興的信息技術產業之外的大量實體經濟企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后果上看, 要為美國大量實體經濟企業后來的長期停滯負責。
80年代,里根當選
美國
總統,嘗試各種手段擺脫70年代末美國陷入“滯漲”的情況,包括提高利率治理通貨膨脹等。
當時,美國在產業競爭層面已處于下風,迫切需要重振實體經濟,包括加快推出新產品和技術升級來應對日本的挑戰。
也的確出現了一些代表性的產業中興功臣,如曾任福特汽車總裁,被解職后臨危受命重振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的李·艾科卡。但是很遺憾的是,80年代中后期的大量因素不利于美國大部分實體經濟產業的復興,里根的供給側革命未能取得預期成效。
盡管后來美國靠信息產業的增量部分及全球化取得了世界的領導權,但大批傳統產業——包括能源、電力、汽車、裝備制造、消費品等諸多產業在后來20多年乏善可陳,而美國的基建趨于停滯并逐漸破敗。
在諸因素中,杠桿收購是非常重要的人為因子,80年代的杠桿收購主要瞄準的是傳統行業尤其是制造業,大部分標的公司除短期內退市再上市中估值提高給收購者帶來財務回報外,在長期都沒能真正復興。

▲ 80年代美國產業英雄李·艾柯卡,在日本汽車長驅直入美國市場時奮起直追
80年代中期起蠶食并長期統治西方傳統制造業等產業領域的金融資本與過去的收購發起者不同,它們不是產業參與者,不用現金或換股并購,也不像60年代的多元化集團那樣用換股收購(60年代美國出現把不相關的企業拼湊在一起的資本游戲,但沒有涉及大規模借貸)。 它們是純財務公司,半路出家,沒有產業運營經驗,也沒有現成的人們愿意接受其股份的公司,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KKR等私募股權(PE)公司。 它們要并購實體經濟的上市公司,用的是環環相扣的高杠桿以現金收購上市公司,通常包括四層:養老基金成為旗旗下并購基金的有限合伙人(LP)、保險公司提供過橋貸款、從銀行借款(并購用途的銀團貸款)、發行垃圾債券(認購者多為當時剛剛解除投資管制的儲貸機構即原住宅專門銀行)。
被收購對象退市后折騰一番再上市。這種金融上的“掃貨”行為連帶激發了股市上的“公司突擊手”(corporate raider)等寄生現象的出現(并購通常使標的公司股價上漲,如提前得到消息可提前布局,專業從事此道之人即為公司突擊手)。 所謂“積極股東主義”盛行于世,大量制造業上市公司被并購和轉賣。 而私募股權公司接手后,由于操盤手并非專業出身,實質上玩的是靠削減研發投入等短期手法粉飾報表再上市套利的路數。 具體的方法是: 在法律上將為并購建立的工具性法律實體和并購對象合為一體,這樣為并購而設立的工具性法律實體所借的大量債務就變成并購對象的債務。被并購的標的企業在退市后,通過大量削減成本——包括日常開支、員工及研發開支來還債。在這一過程中,因為還債有利息,而債務總量大大高于并購前,因此退市后起先利潤會很低,但避免了稅收——因為利息在交稅前扣除,而原來公司被并購前沒有高負債也就沒有這筆利息,那這筆現在變成利息的錢以前是要交稅的。 隨著本金和利息在全力榨取標的公司現金流下逐漸償還,凈利潤就重新增長,這樣形成一個長達兩到四年的優質增長的凈利潤記錄,再拿去上市。
當時,由于擺脫了70年代的高通脹, 從1983年起,美國資本市場形成一個持續的牛市,估值得到提高。在這一期間如實現退市、再上市,市場市盈率中樞本來就在提升,同時還做出一個再上市前增長的樣子,就可按增長股估值,如此賣出,并購基金就賺錢了,而私募股權公司(管理方)更是從第一天起就在個人意義上賺的盆滿缽滿。 正是因為大家都看到這種新型的發財秘訣,所以美國80年代各路人馬都紛紛建立并購基金,開展杠桿收購業務。
?主要是因為美國當時的管理結構正好處于一輪青黃不接的狀態 ——大部分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前期創立的大中型企業創立者及其家族多已退居二線,經過60年代的管理層接管,大部分企業的經營波瀾不驚。
另外,80年代初時任美聯儲主席沃爾克治理通脹時提高利率也讓一些行業經營困難,80年代中期大量制造領域的美國企業全面受日本沖擊,非常窩囊。這時有一批像《華爾街》電影的蓋柯這樣的振臂一呼,“貪婪就是好”,又 在并購中給散戶和共同基金等原有股東甜頭,這些群體得到了短期甜頭,自然樂見其成。但是,這種并購并沒有提高企業和所在行業的效率。 有些經濟學家拿并購資本進出前后的利潤水平來證明私募股權基金“提升了經濟效率”,這是錯誤的,因為這本身就是靠削減成本尤其是長期研發投入人造出來的利潤。如并購型PE有“絕招”,那么其一不應該人人都能做,只有少數有絕招的人能做,其二應該不受時間限制,但事實上并購型私募股權基金的繁榮非常集中在特定時間段:包括80年代中后期、2005-2007年和2013年以來的一些時間。這顯然是因為它主要抓的是外部資本市場環境帶來的紅利,而當環境不利時(比如90年代初),它們就一窩蜂退卻到相對保守的美國房地產REITS領域了。
并購,作為企業叢林中一種常見行為,本來是中性的——但并購后的整合從來都是十分艱巨的任務。 有價值的并購是發動并購者和被并購者互有所需,在整體上能提高產業效率,比如一些本身太小但有獨到技術的公司通過被并購整合到具有系統能力的大中型企業里面發揮價值。因此,這種并購一般由產業公司發動,在產業內進行。但 美國80年代的杠桿收購 是純財務公司并購實體經濟企業,而且大規模動用杠桿(而非自身現金或換股并購),為了讓高杠桿、高利息的債務得到償還,勢必要削減研發等長期投入,很顯然,這 在本質上沒有對企業的長期研發尤其是長期戰略路徑進行什么考慮,這樣一種短期操作,對企業少有改進,甚至摧毀了企業的長期研發體系。 事實上,李·艾科卡等產業英雄就非常厭惡這種行為,在其自傳中專門對此類并購及寄生其上的各種訛詐公司的“豪杰”給予譴責。但是 很遺憾,美國大量產業都多多少少被這種私募股權并購基金所染指,平庸是這些產業近30年的主要特點,這一規律在當前中國企業在海外并購一些公司時都能發現。
當前中國“舉牌”現象,與80年代美國杠桿收購有類似性
由于法律不同,中國財務投資者尚不能通過設立專門法人實體,借債并購實體。但是保險領域的萬能險卻為類似的行為提供了管道。 保險公司具有理財產品性質的萬能險產品,和美國杠桿收購中的舉債是類似的,只是利率相對較低,可以事實上實現滾動操作,不要求硬性還債而已,另外, 中國的舉牌不需要收購全部股權,只需要實現成為上市公司的大股東(對那些股權分散的公司,通常20%以上即可)——但是,這顯然是指向參與企業決策尤其是財務方面的決策,否則也沒有必要執意舉牌成為大股東。 可見,中國舉牌現象和80年代美國杠桿收購在性質上類似,美國的教訓我們就不能不警惕。
2015年底,中國資本市場發生寶萬之爭,只不過萬科本身是中國過去20多年比較容易賺錢的房地產行業,其領導人也確有長期脫離企業去游學等易讓人詬病的問題,因此其不利影響還不很凸顯,但 2016年以來,一批改革開放以來具有技術領頭人意義的制造業中堅企業由于股權分散,被新興激進型保險公司舉牌并產生一系列變動,這就值得人們警惕了。 前幾年,中國平安入住上海家化,很快就導致這家經營不錯的地方國企逐漸平庸,已經是前車之鑒,最近又有改革開放陣地深圳的知名企業南玻因舉牌而來的保險公司大股東干預企業創始團隊的重大戰略而導致團隊出 走,非常讓人警惕。這 當然是社會福利的損失。 現在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靠理財產品裹挾大量資金的“門口野蠻人”對格力電器、特變電工這樣的由能人一手領導帶大,具有重要科技產業制高點意義,同時因為出身集體所有制而股權分散的公司進行“舉牌”,進而影響企業戰略軌跡。
讓中國版門口的野蠻人肆意任為,勢必對這些對國民產業高地至關重要的企業產生負面影響。前文所提,美國杠桿收購的最危害是并購后,標的企業為了償還發動收購者借的債,削減了長期研發投入,指使技術停滯和長期國際競爭力下降。 中國舉牌的潛在危害就是財務投資者控制實體經濟公司,片面要求高分紅。 當前被瞄上當作目標的企業,多半是在某領域已經取得重大成就,相對行業其他企業利潤水平較高,規模較大但市盈率水平較低的優質企業。 現在很多舉牌者或暗自竊喜于舉牌行為的投資者,盼的就是“現金牛”——你企業已經有這個位置了,那就應該多“回饋股東”。這種理解是錯誤的。 在這一點上,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不要生搬硬套流行理念,比如巴菲特喜歡現金牛的價值投資,實際上是不對的。巴菲特投資組合中的真正現金牛只有喜詩糖果這樣的孤例,而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技術不進步的產業,美國大部分產業不是這樣的。事實上巴菲特的幾個典型成功投資案例,在其入股時并非高分紅企業,而是反復投入發展的增長型企業,如麥當勞、可口可樂等。
事實上,從長期看, 并不存在能永遠當現金牛的企業,因為企業經營是有起伏的,每時每刻都應當為3-5年后的市場及產業環境做好準備 ,如果不做好準備,不投入研發,不涉足更新的領域,那么擠壓出來凈利潤去進行所謂高分紅往往難以持續5年。按中外經驗,企業分紅率,以市值為分母,每年達6%已經算很高的(更多的是當年凈利潤的30%-50%多,一般相當于市值的1-2%,更多要依靠企業股權價值的增長來回報投資者), 假設連續高分紅5年,也就分出5年前市值的30%,如企業因為沒有早做準備而逐漸競爭力蛻化,市值也會縮水,對投資者其實是得不償失的。 而在中國式舉牌情境下意味著,那些購買了理財產品的投資者的產品價值縮水或兌付無法維持的風險。
中國中堅力量企業進入發展關鍵階段,企業長期發展不應受到舉牌者的干擾
當前, 中國正在進行供給側改革,迫切需要有新的,有技術含量的增長點擺脫過去幾年社會沉迷于房地產、理財及少數通過擊鼓傳花高估值的暴富行業帶來的泡沫困境。因此,中堅力量企業非常重要。而我國恰好有相當一批企業發展到了關鍵階段,正處于群體崛起的黎明時刻。 這里面有一批大型企業,正在向類似通用電氣、西門子、飛利浦這樣的歐美實體經濟鼎盛時期的專業多元化企業集團躍進,從一個起點出發,以觸類旁通但不斷進取的態勢,不斷開拓新的技術應用邊疆,這里面包括中國中車、華為、比亞迪、特變電工、格力電器、京東方等企業,同時又出現了一批在專門領域非常專注,不斷在更新替代的上游專門領域拓展的企業,比如歐菲光、康得新、濟南二機床、均勝電子等企業。 從企業經營上看,企業的拓展是需要股權支持的,因此,除華為、濟二機床等少數特殊案例外,大部分企業是需要資本市場支持的。 這也是企業成長價值為社會分享的題中之義。而其中很多成長歷程非常迅猛的企業,往往是基層成長的強人主導,這種基層人物肯定要充分調動各種力量,因此歷史形成的股權結構比較分散。
從一些中國企業典型的案例看,大批企業正在進入重大新產品研發或重大戰略決策階段,這是呼應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是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機組成部分。 這些重大產品研發和戰略選擇,往往需要耗費2-5年時間(指物質領域或真正高技術領域的新產品,不包括媒體性的互聯網“產品”),一般3年比較常見。而且越是從無到有的越難,越是沒有國外先例的越難。 目前已經發生的案例,如康得新搞增光膜、歐菲光搞新型觸摸屏、攝像頭模組,2-3年;比亞迪從無到有搞“云軌”,5年;京東方搞擴產走出困境,3年;特變電工搞超高壓、特高壓產品,3年左右;華為從提出“云、管、端”搞高清圖像傳播,研發了三四年。
很多企業一手在推廣已經取得的成功,一手又在進行下一步布局,比如上述企業已經投入到碳纖維、指紋模組及芯片、OLED等等下一代產品中去。 中國的中堅企業將長期處于多代產品迭代式研發,多領域同時研發等情況,不可能片面成為所謂“現金牛”。 即便是資本市場最被認為是所謂現金牛的水電企業,也涉及再投資開發新水電站的戰略要求。把公司資金片面用于高分紅,和美國杠桿并購把稅前利潤以利息形態轉移給貸款者一樣,是一種系統性的把實體經濟用于下一步的長期資金轉移給在意短期利益的金融資本或金融受益者的做法,不利于社會長期發展,尤其不利于當前中國處于關鍵階段的供給側改革。
從舉牌涉及雙方對企業發展的作用來看,舉牌行為干涉企業經營也是不能接受的。一邊是辛辛苦苦做了20年乃至30年的企業,一心為企業長期發展著想(比如格力電器董明珠,比如南玻的曾南)的能人;一邊是對外發理財產品,短時間內囤積幾十億、幾百億的現金,被堆著的現金推著“不得不”到處搜尋大規模投資對象,“不得不”舉牌眼中的“類債股”的純粹財務機構,誰會為企業長期命運著想? 誰有能力為企業重大戰略決策負責,為企業百年基業不斷培養出一代又一代團隊,使能人代代傳承?答案是很清楚的。 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的是一批不斷傳承的,干預為人類開拓新邊疆的產業企業家群體,而不是進行純粹財務運作的資本弄潮兒。我們要記住,企業不是某些“養豬理論”所說的豬,“養大了就要賣”,對于有技術門檻的企業來說,企業就是企業家的生命,這在中國產業升級的深化改革過程中,只會加強,不會減弱。
強基固本:珍惜企業家,強化實體經濟領導團隊話語權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對中國國力的強基固本,立足長遠的產業企業家是中國未來的中堅力量,因此在資本市場相關規則上,誰主誰次就應當明確。不能僅僅以舉牌方口頭承諾為界,需要進行明確的法規約束。
中國資本市場乃至非上市公司中一些規定,其實是歷史的產物,環境隨歷史發展而變,規則也自然應當做相應的改變。 以同股同權(投票權)為原則的法規,是在90年代初制定的,當時主要是為了防止出現國有資產因為內部人勾結而流失的情況而設。顯然不再適用于當前的情況。尤其是考慮到舉牌的激進保險公司及關聯方的錢實際上不是它自己的,而是“高息攬存”而來,那么這種過于激進的資產管理者就不應當因此獲得上市公司董事會的投票權。 請記住,激進舉牌者的角色與普通的機構投資者是不同的,因為普通的機構投資者如共同基金,總體而言是被動投資者,并不會主動干涉企業的決策。
保證經營層穩定和戰略決策的例子有很多 ,比如德國的監事會就有很大權力。在投票權上可建立相關法規,如規定,短時間內激增擁有大量股權的金融企業將喪失投票權,或單個金融相關集團(含自然人及其親屬控制的不同法人及其關聯企業)投票權,無論其股權綜合超過多少,不超過10%。這樣保證如果某投資者或金融集團特別看好某個企業,可以不斷持股,但沒有投票干預對方經營的權力。另外,可以考慮高級管理人員的投票權若干倍于持有股權,引入美國的A、B股制度或考慮某種法律對接接口實現這種效果。
當前,中國供給側改革將進入攻堅期、關鍵期,國際上特朗普上臺,國際前景不明,美國可能走上固本強基的發展道路,中國面臨資本外流、外匯儲備縮水等系列挑戰。此時,中國理練好內功,保護好自己發展的中堅群體,絕不能大意放縱,讓投機資本在國內各個資產領域不斷掀起風浪。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資本市場不應該急切的鼓吹牛市,更不應當以舉牌藍籌股為由頭鼓吹牛市。中國及中堅企業發展和改革的關鍵階段,不應放任自己內部蛻變出的“野蠻人”敲門干擾。
- 104 1 孔令強:客觀看待當前債券市場違約風險
- 102 2 需求激增 鋰電池概念股進入活躍期
- 101 3 A股難發“入場券”,82家中企赴港掀熱潮
- 100 4 半年報股東榜搶先看:資金在加倉哪些公司
- 100 5 A股回暖是否可期?
- 97 6 客觀看待當前債券市場違約風險
- 97 7 從歷史數據看A股機遇
- 94 8 多部委多地推出新舉措 補短板成穩投資重要抓手
- 94 9 地緣風險及供求缺口或將繼續推高油價
粵ICP備16012416號